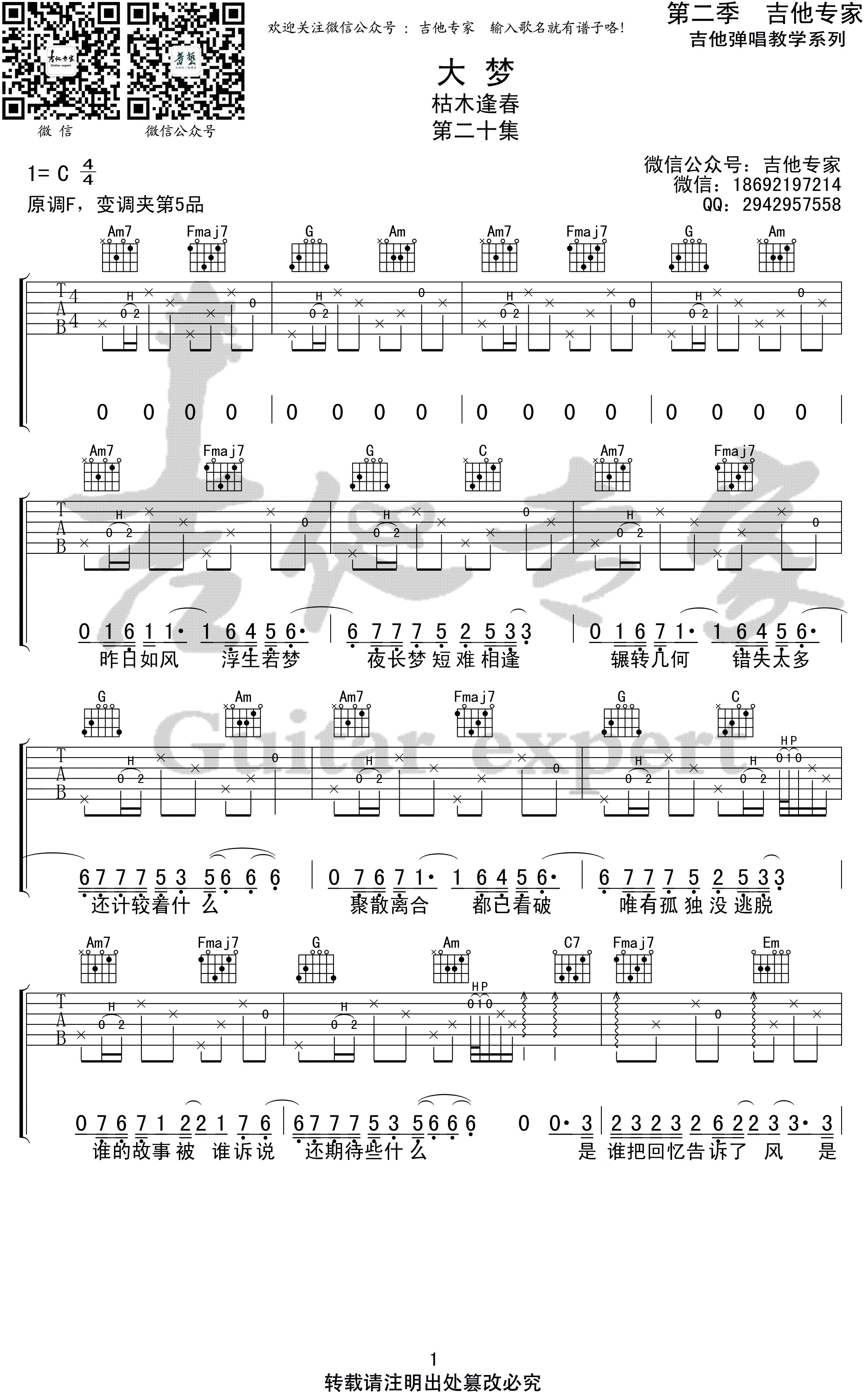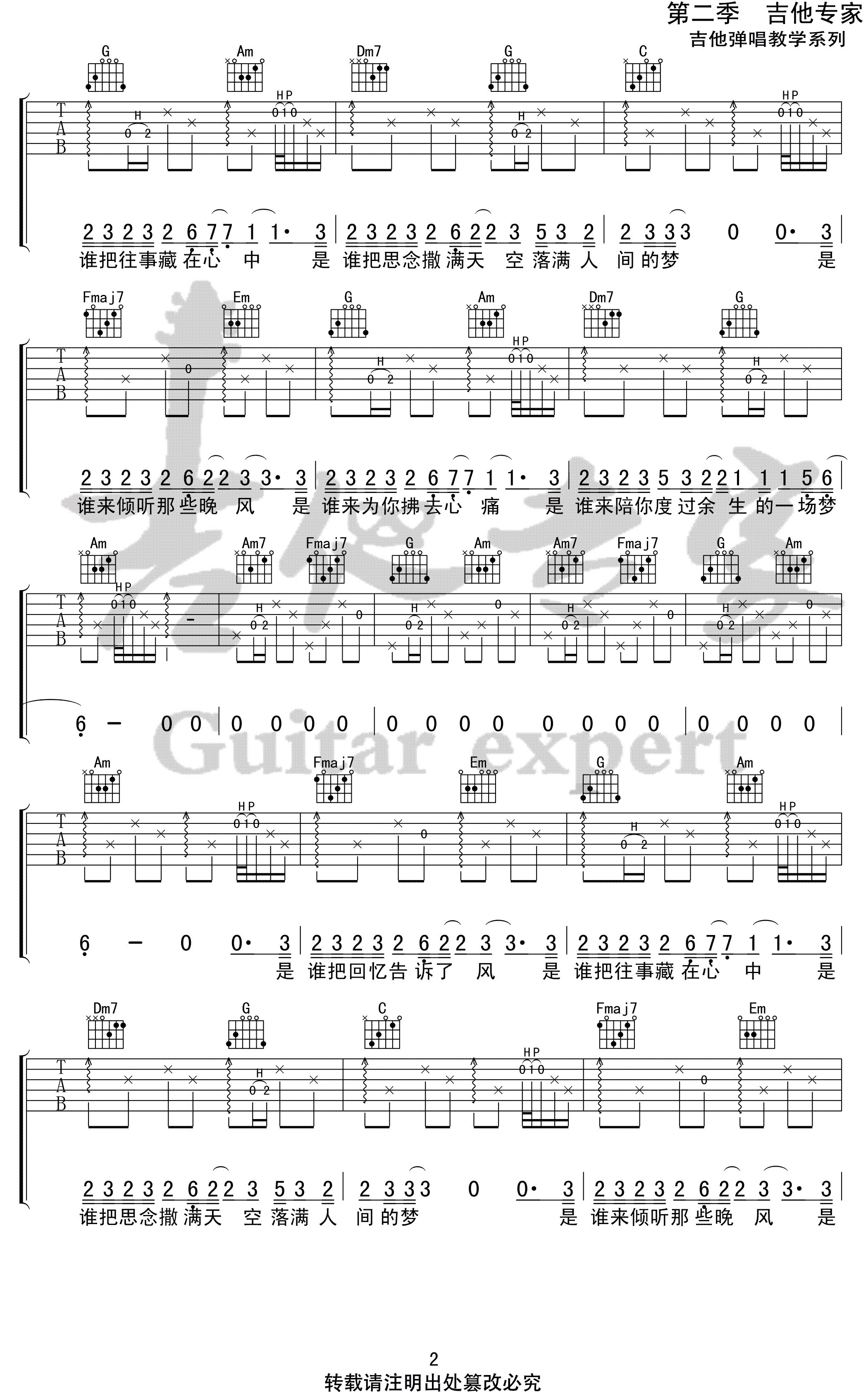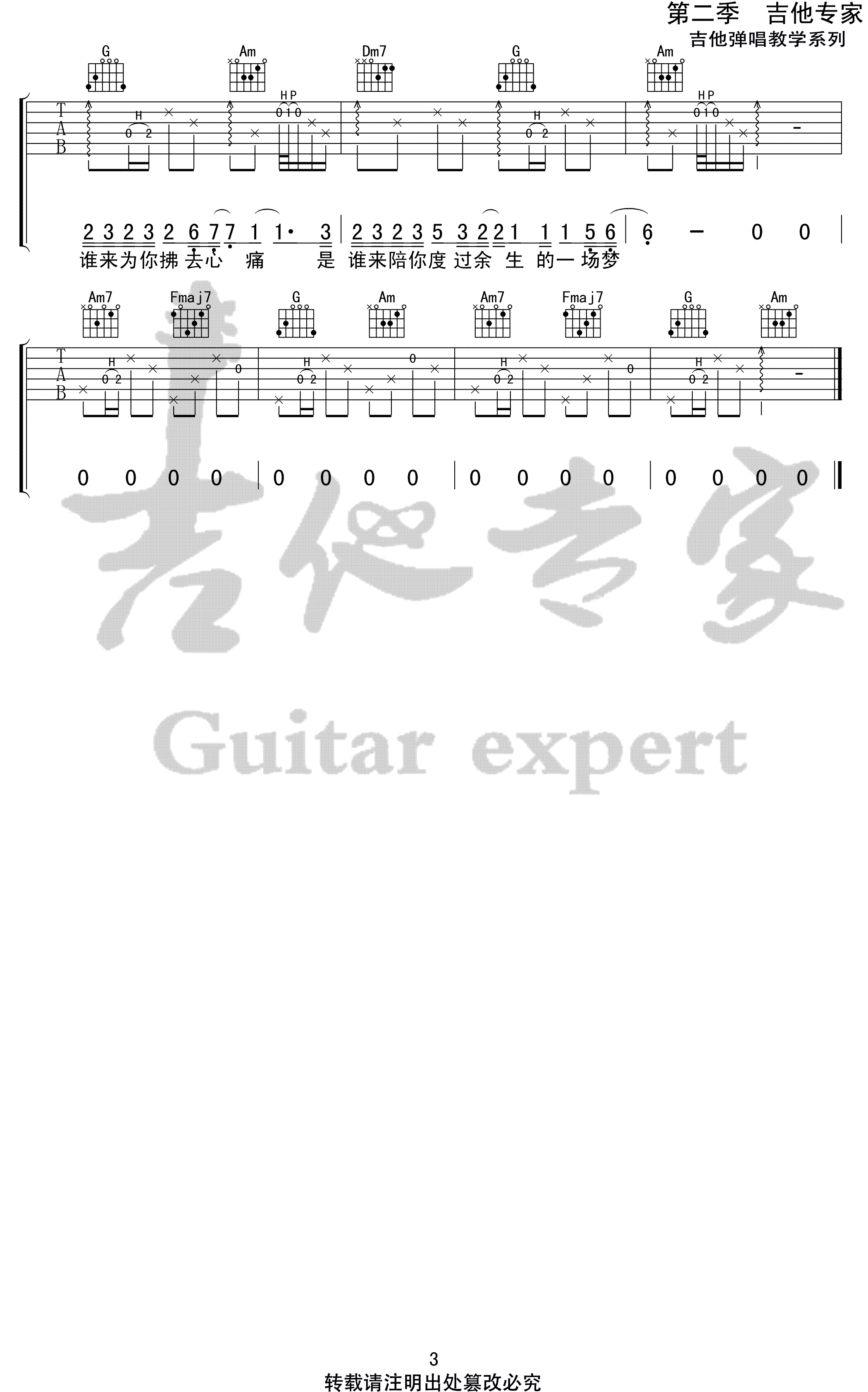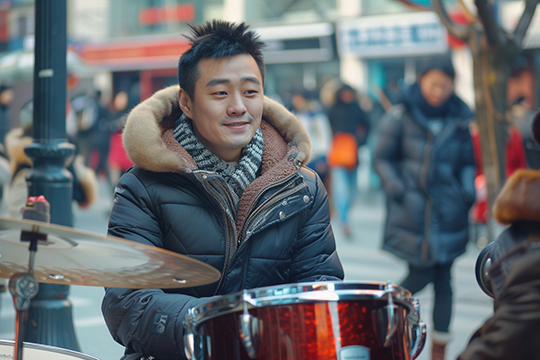《大梦》以绵长的意象与循环的结构构建了一个关于生命本质的追问场域。歌词中"八十八年"的重复并非简单的时间堆砌,而是通过数字的递增展现人生各阶段的困顿与迷思,每个年龄截点都像一面镜子,照见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。昼夜交替的意象与"看天色将晚"的反复吟唱,暗示着时间流逝的不可抗力,而"睡梦"与"醒来"的二元对立则构成存在主义式的诘问——当个体在柴米油盐的生存压力与爱恨别离的情感羁绊中辗转,生命的本真状态究竟在梦境还是现实。歌词中不断出现的"该怎么办"并非具体困境的求助,而是对生存焦虑的哲学思考,如同《红楼梦》"好了歌"对世俗价值的消解。四季轮回的意象与"眼泪流下来"的细节描写形成宏观与微观的时空对话,当所有具象的苦难最终归于"大梦"的隐喻,实际上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的禅意解构——正如庄周梦蝶的古老寓言,歌词最终模糊了幻梦与真实的边界,在循环往复的诘问中,答案或许早已藏在问题本身。这种东方哲学式的表达,让具象的生活片段升华为普世的生命体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