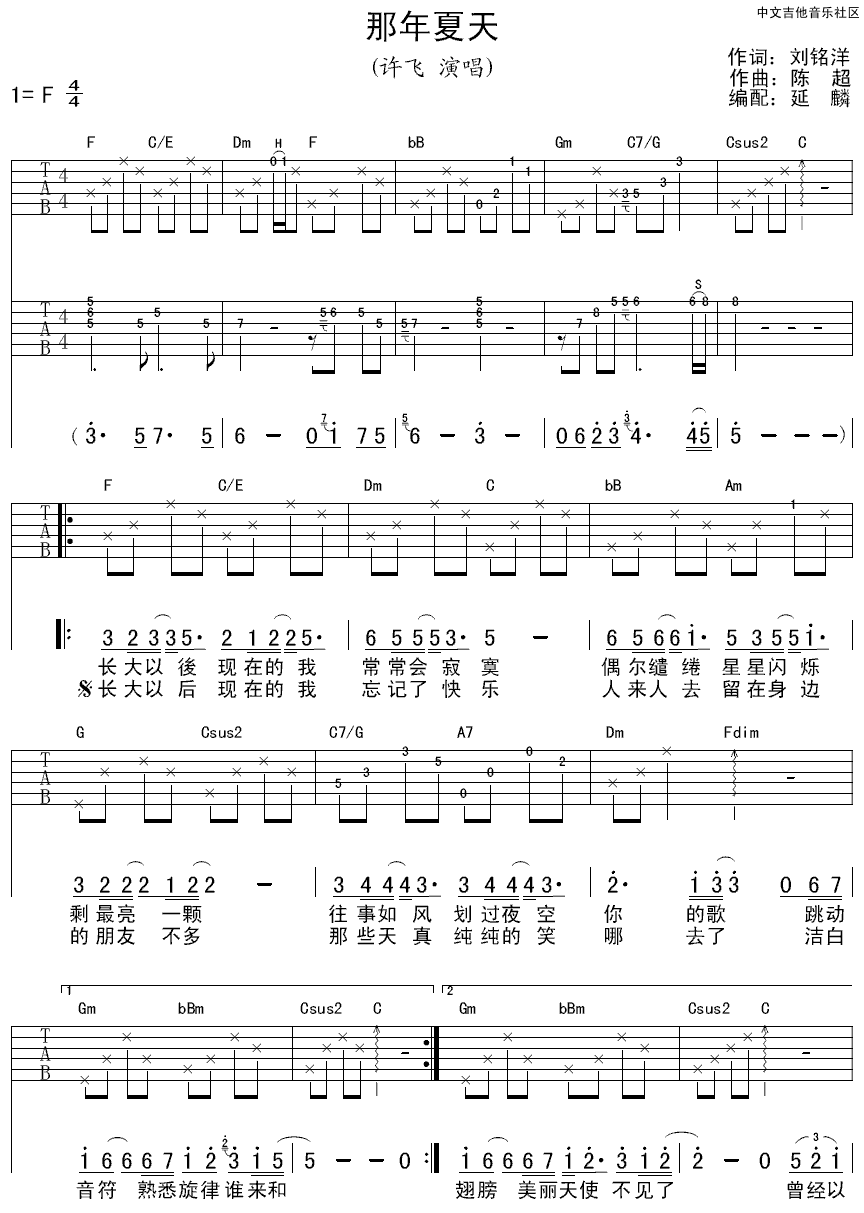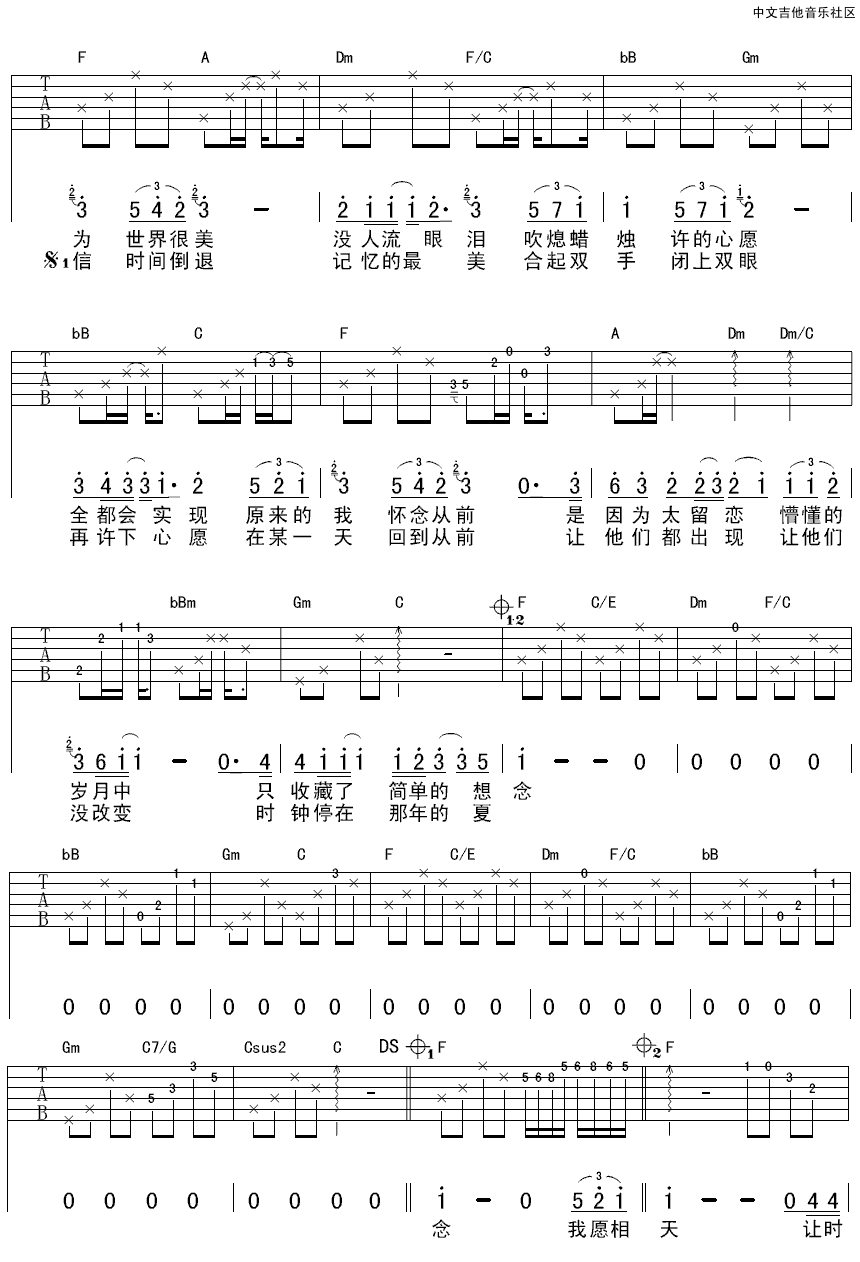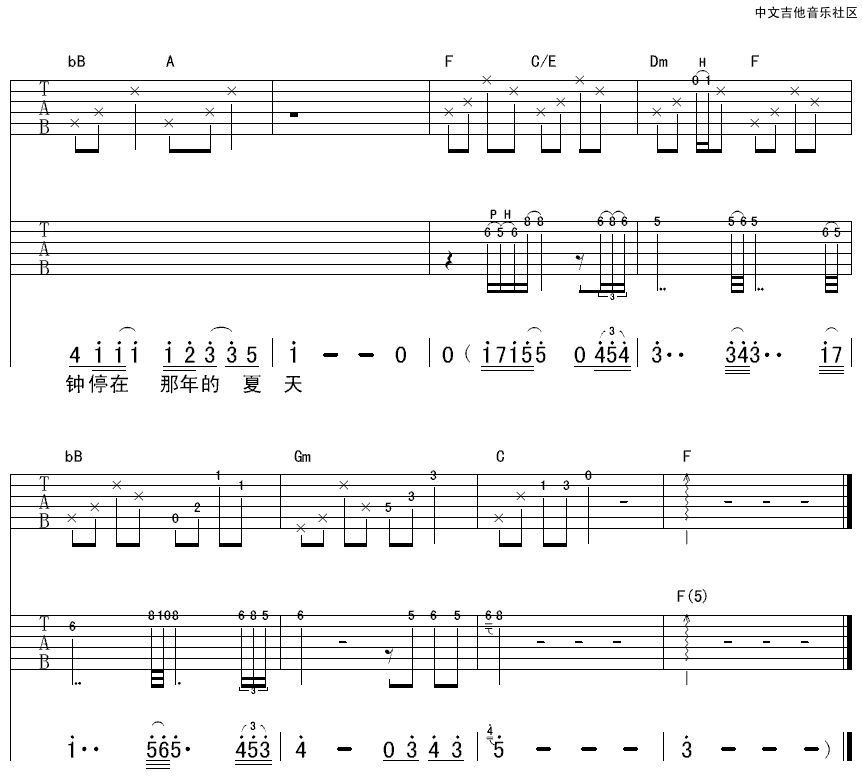《那年夏天》以清新质朴的笔触勾勒出青春记忆的朦胧画卷,蝉鸣与树影交织的意象群构建出典型的夏日场景,却暗藏时光流逝的怅惘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自行车铃声、冰镇汽水瓶的水珠、操场边的白球鞋等具象符号,既是青春物证的陈列,也是情感载体的隐喻,在看似琐碎的细节里埋藏着集体记忆的共鸣点。通过"未完成的告白信在抽屉泛黄"与"黑板擦落下最后一粒粉笔灰"的时空交错,展现记忆特有的蒙太奇效果,将遗憾与美好并置于同一情感光谱。副歌部分对蝉声的反复咏叹形成听觉记忆的锚点,而"我们"作为集体代称的消失,暗示着成长必然经历的离散。歌词擅用通感手法,让汽水的甜味与汗水的咸味在记忆中发酵,最终凝结成"晒褪色的明信片"这一视觉象征,完整呈现了记忆从鲜活的动态体验向静态标本转化的过程。全篇避开了直白的抒情,转而通过物象的排列组合,让夏日的光斑与阴影自然投射出青春的短暂与永恒。